策劃語 軍人是祖國的脊梁,是祖國的忠誠兒女,他們是最可敬的英雄。報效國家,是中華男兒的錚錚誓言;獻身使命,是鐵騎雄兵的無悔信念。他們無私無畏,劍膽琴心;他們忠誠奉獻,鐵血柔情。昨天,他們曾浴血奮戰,青史留名;今天,他們又威震天下,守護和平。軍人把詩情寫在江河湖海,把豪情刻在高山峻嶺。八一,是軍人的節日,讓我們聽他們講述自己當兵的經歷,講述自己從軍的感受,講述軍旅生涯對自己人生的影響——
策劃人 韓曉芳
孔貴林:炮火伴我“成長”
臨汾新聞網訊 “經過烽火硝煙的戰爭歲月,靠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我活到了今天,對我來說,無論工作還是生活,都沒有任何困難能打倒我,這是我一輩子受用不盡的寶貴財富。”回憶起那段畢生難忘的特殊經歷,眼前的耄耋老人孔貴林不禁思緒萬千。
我要去當兵
86歲的孔貴林,家住堯都區車站社區。
童年時期,由于家中貧窮,正值壯年的父母生病后無法醫治,相繼離開人世。四個已為人妻的姐姐也生活艱難,12歲的孔貴林只得被送到同村一戶姓王的地主家當起了小長工。
“記得那時,不管寒來暑往,只要每天雞叫頭遍,我就要起床割草、墊圈,稍有不慎就會遭到地主的一通毒打,生活過得異常艱苦。”直到1947年,17歲的孔貴林迎來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個“轉折點”。
孔貴林說,那年,村子里來了一支“不同尋常”的部隊。“他們對老百姓非常熱情友好,還主動幫窮人掃街、挑水,幫我在牲口棚里墊圈。他們告訴我,有朝一日解放了,政府還會給窮人分田地、分房子,讓大家都能吃飽飯……”這樣的話語如同一盞明燈,點燃了孔貴林心中的希望之火——我要去當兵!為窮人求解放、謀幸福。
炮火中前行
隨后,經人介紹,孔貴林穿上了軍裝,加入了當時的襄陵縣縣大隊。大字不識一個的他開始拿起筆,跟著文化教員一字一句地念,一筆一畫地寫。
1948年年初,臨汾戰役即將打響,孔貴林所在的襄陵縣縣大隊奉命為大部隊做好后勤工作。用孔貴林自己的話說:看著人家扛槍上戰場,咱只能干好運糧食、抬擔架的活兒,心里還真有點不服氣。”
“看出了我的‘心思’,一天,班長把我帶到了一座廟里。一進門,眼前就是一排黑漆漆的棺材,攻城敢死隊的隊員們正在開誓師大會。”回想起當時的場景,孔貴林不禁淚濕眼眶。只見隊員們慷慨激昂,大家咬破了自己的手指,用鮮血在每個棺材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
“我要安心做好后勤工作,讓前線戰士無所顧忌地沖鋒陷陣。”1948年3月,臨汾戰役正式打響,奉命守在城西門口收容逃兵的孔貴林雖然沒有親自奔赴前線參加戰斗,但關注戰事的進展,成為他心中的頭等大事。
臨汾解放后,孔貴林所在的襄陵縣縣大隊經整編,被編入一野十八兵團司令部警衛營,跟隨大部隊南下過黃河,進軍四川,開始剿匪戰斗。
1950年,大部隊過黃河后,便一路南下,打咸陽、攻寶雞……孔貴林說,當時,國民黨的部隊潰不成軍,兩軍相遇時,他們常常虛晃幾下便開始逃竄。那時,我只能緊追而上,有時一天行軍上百里地,戰士們腳都腫了。白天行軍口渴時,看到地上坑坑洼洼的積水,撥開柴禾用手舀起來就喝。”說起當時的情景,孔貴林頗為激動。
如今,退休后的孔貴林老有所為,發揮余熱,作為社區關工委輔導員時刻對孩子們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用他的話說:愛國教育從娃娃抓起,黨給了我幸福的生活,我就要回報社會,感恩祖國。”
記者 成華
廉建忠:大熔爐里煉真金

臨汾新聞網訊 今年53歲的廉建忠曾在大西北某部隊服役13年,他參與過多次科研試驗。于他而言,當兵才知道帽徽為什么這樣紅;當兵才知道肩章為什么這樣重;當兵才知道祖國的山河在心中……
1981年9月,他從軍校畢業后,被派往祖國的大西北。那時,中國百業待興,正是用人之際。他所學的知識能夠派上用場,著實令他激動和興奮。
當時,駐地周圍是渺無人煙的戈壁荒漠,一刮起風來,漫天黃沙飛舞,十米之內的事物都看不清。服役期間,廉建忠走得最多的就是砂石路。每每遇上這樣的刮風天,路上的石子亂飛,他和戰友經常被亂石誤傷。即便自然環境極其惡劣,生活條件相對貧瘠,他依然不忘初心,并暗暗許下心愿:只要祖國需要我,我愿一生扎根于此。”
最令廉建忠引以為豪的便是,他曾多次參與科研試驗。“我所學專業與國防科技有關。雖然當時大多流程已實現機械化,但仍需要人工與機械完美配合。這對人員素質與技術要求非常高,每個步驟都不能有絲毫差錯。在那兒工作從沒考慮過個人安危,就算面對生死抉擇,只要能為國家作貢獻,我們都會毫不猶豫地沖上去。”他回憶著難忘的一幕幕,不由心潮澎湃、熱血沸騰。
“從踏進軍營的那一刻起,每個人已經站在了一條不同于常人的起跑線上。在工作和訓練中,一定要積極刻苦,不要怕苦怕累,軍人是要保家衛國的。沒有知識武裝自己,沒有過硬的軍事素質,還談什么打勝仗。”歷經13年考驗,他從普通士兵升至連長。在浴火淬煉中,他練就了鐵打的骨頭,結下了生死的戰友情誼,更鑄成了為祖國、為人民一切行動聽指揮、甘愿犧牲奉獻的鋼鐵信念,表現出了和平年代軍人崇高的榮譽感與責任感。
1994年,廉建忠轉業回地方,進入原臨汾地區郵電局工作。此后,他不論身處任何崗位,都積極發揮自身的作用,努力在工作上實現突破、達到極致。回顧自己曾收獲的榮譽及為單位作的貢獻,他堅定地認為:“部隊鍛煉的堅強意志、頑強毅力、強健體魄,是一生最大的財富,更將是今后人生的基石。”
“人生中有了當兵的經歷,一輩子也不后悔。當兵的意義究竟在哪里?保家衛國,磨礪人生,收獲無價的精神財富。”13年的軍旅生涯,鑄就了廉建忠的錚錚鐵骨。這段經歷是他生命中最榮耀的記憶,大西北也是他魂牽夢縈的第二故鄉。而“艱苦奮斗,無私奉獻”的精神早已注入他的血液,時時激勵著他奮發前行。
記者 李靜
賈林林:紅星照我去戰斗

郵運車就是賈林林新的戰斗崗位。
臨汾新聞網訊 今年36歲的賈林林,是我市郵政分公司的一名郵運車司機,他最喜歡的一支歌叫《紅星照我去戰斗》,因為這支歌,他在上世紀90年代末,走進部隊,成為一名光榮的武警戰士;又因為這支歌,讓他在退伍之后,甘于走上平凡的崗位,默默無聞地為人民服務。
“我其實只是一個很普通的人,你要采訪我,我也不知道該說些什么,我只是始終以一名軍人的標準要求自己,不管是在部隊,還是在郵運車上,都努力站好崗。”雖然離開部隊多年,但賈林林在部隊里養成的直爽性格始終沒有改變,他表示,雖然離開了部隊,但自己始終懷念部隊的生活。
1999年,18歲的賈林林剛剛高中畢業,從小就向往“穿軍衣、戴軍帽、配大槍”的他,說服了家人,來到太原成為省城武警某部的一名新兵。“我其實想去更遠的地方當一名解放軍,但是那一年臨汾招的兵都是武警,我就去了武警部隊。”賈林林告訴記者,在他的印象中,軍人,是一份很嚴肅的職業,每天腦袋里就應該想著如何戰斗,如何勝利。可真正到了部隊后,他卻發現,軍人的首要責任,是維護和平、為人民服務。
“當兵第二年,我們部隊集訓醫護兵,我被選中并參加了集訓。自那以后,我的肩膀上就多了一個代表醫護兵的紅十字,一直到退伍。”賈林林說,最開始他不愿意去當醫護兵,也不想去集訓,因為在他的眼中,兵就該拿槍,背著急救包、手里拿著包扎帶算怎么回事?可班長后來找他談話,告訴他,醫護兵是一個戰斗小隊中頗為重要的角色,要想當醫護兵,需要得到所有戰斗員的信任,這是榮譽。而作為一個兵,就應該堅決服從命令。
2002年,賈林林退伍后被安置到市郵政分公司,成為了一名郵運車司機。“我在部隊養成了服從命令的習慣,上班之后,這個習慣一直沒有改變。”賈林林說,作為郵運車司機,每天的工作就是要按時將各種郵運品運送到鄉鎮,然后再將鄉鎮發出的郵件運輸回公司分揀車間。
這是一份簡單的工作,也是一份平凡的工作,但是就是在這個工作崗位上,賈林林做出了成績。“最初當兵是因為我對軍人職業的向往,到了部隊后明白了軍人的職責,現在我也要將這份工作當成自己的職責。”賈林林說,在我負責郵運的河底鄉,距離市區有二十多公里,在去河底鄉的路上,經常會遇到鄉親們徒步去往市區,如果方便我便會將他們捎上一段。”
“如果沒有當過兵,我想我不會多管閑事順路捎他們,但我當過兵,知道什么叫為人民服務,所以我才會那樣做。”賈林林說,在部隊的生活只有三年,但卻是讓他脫胎換骨的三年,在部隊里,他學會了承擔責任,知道了什么是義務,知道了什么是堅守崗位。如今,他離開部隊十幾年了,可當兵時的那股子勁頭始終伴隨著他,那首《紅星照我去戰斗》的歌曲,始終激勵著他前行。
記者 楊全
楊宇:逆行身影別樣美
臨汾新聞網訊 人人朝著生門跑,你卻迎著火光沖,那一身顯眼的消防服,讓世界記住了你啊消防兵。逆行啊逆行逆流而沖。使命更比生命重。逆行啊逆行逆流而沖,你逆行的身影,就是一道最亮的風景……這首歌是歌頌消防戰士的。八一前夕,記者采訪了一位消防指揮員。
楊宇,1983年出生,襄汾縣汾城鎮人,2000年12月入伍,被錄取到長治消防支隊,成了一名普通的消防戰士,2002年考入河北廊坊市武警學院,2005年9月被分配到洪洞縣武警消防中隊任副中隊長,現為霍州市武警消防大隊教導員及臨汾市滅火救援攻堅組負責人。
“我喜歡當兵,當兵是我從小的夢想,那時候到照相館照相,我總是選軍裝,看電影也總愛看戰斗片。”就是這樣一份熱情,促使楊宇走進了部隊,但入伍前,他對消防兵根本不了解,直到穿上這身軍裝,他才知道消防兵的職責是什么。
在楊宇從軍的十幾年中,經歷過無數次的搶險救援,選擇了無數次“逆行”。
2007年的一天,一輛特種車在運輸途中出了車禍,氨氣泄露,楊宇和戰友們從洪洞馳援,老遠就能聞到氨氣刺鼻的味道,事故車周圍果樹的葉子都被熏的發黃發黑。“最厲害的部隊來了!”在群眾的企盼中,楊宇和戰友們義無反顧地用堵漏膠去封堵大約20厘米長的裂口,但是車內壓力太大,漏氣的裂縫并不好補。兩個戰士上去都沒有補好。楊宇一看,立刻沖上前去,將戰士替換下來,一次、兩次,裂口還是不好補,情急之下,楊宇索性摘掉防毒面罩直接操作,全然不顧氨氣對身體的危害,終于將漏氣之處嚴嚴實實堵住了。
“當然,我們也會后怕,但當時不會去想危險不危險,唯一的念頭就是執行命令、完成任務,最滿足的時候是任務完成后群眾給予的贊譽與掌聲。我喜歡消防,喜歡那種成就感與榮譽……”楊宇對自己的職業十分自豪。
直到現在,從戰士成長為一位中校,楊宇最愛看的影視作品還是軍事題材。“現在帶兵了,我最愛看的電視劇是《亮劍》和《士兵突擊》,致力于打造一支‘嗷嗷叫’的部隊,我帶兵最在意的就是‘精氣神’,部隊崇尚的是集體主義精神、革命的英雄主義氣概,我最喜歡的是那種‘不拋棄不放棄’的感情。消防戰士訓練時都是以秒計算的,平時,戰士們訓練確實很累,我也很心疼,但是,只有平時多流汗,戰時才能少流血。”現在帶兵,楊宇更多地體會到“嚴是愛”。
工作幾年后楊宇又被分配到霍州,由于當初霍州消防基礎差,他心里很不情愿,可是,幾年鍛煉下來,楊宇深深地喜歡上了這里。再大的成就也經不住一把火。”楊宇初到霍州時,很多百姓甚至不知道火警是119,有的還會問,滅火要多少錢?”為了讓消防深入人心,楊宇十分重視宣傳,如今,霍州市最大的廣告牌宣傳的是消防,出租車頂燈宣傳的是消防,就連圍裙上都是消防宣傳,大媽們跳廣場舞穿的T恤上也是消防的內容,他就是想讓每個公民都樹立消防意識,時刻注意防火。如今,霍州消防大隊已經成了全省的優秀大隊。“我喜歡挑戰,閑不下來。初來時,霍州消防甚至連正式的辦公場所都沒有,如今,在霍州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霍州消防大隊建設了全臨汾市面積最大的訓練場所,有10層訓練塔、室內訓練館、還建起了消防主題公園、消防主題社區、消防文化一條街,目前,54米多功能登高平臺已經在招標中,第二消防站也在籌建中。”楊宇說。
消防,是和平年代最危險的行業,火情面前,什么意外都有可能發生,面對一個個陌生而又充滿危險、亟待救援的場所,楊宇帶著他的隊伍從來沒有畏懼,沒有退縮,總是力求把群眾的損失減到最小。他說:“我喜歡穿軍裝,穿上軍裝的感覺就是不一樣,那是一種責任、一種榮譽,既然當了兵,就要像個當兵的樣子,就不能對不起頭頂的國徽,不能辜負這身軍裝,不能辜負領導和群眾對我們的期望。”
記者 韓曉芳
楊繼明:三代軍人 傳承愛國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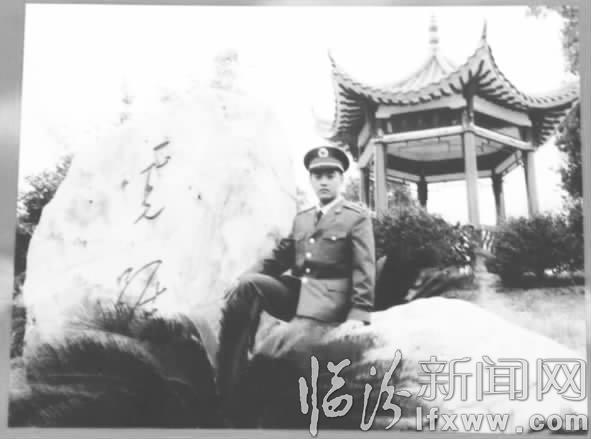
楊寬近照
臨汾新聞網訊 提起楊繼明一家,臨紡社區的許多住戶無不流露出敬佩之情,因為他家是三代黨員、三代軍人的“光榮之家”。
7月27日,記者在臨紡生活區見到了楊繼明。
提起一家三代軍人,楊繼明告訴記者,最令他自豪的有三樣東西,一是父親留給他的軍功章,二是他當兵時的五星帽徽,三是兒子考上軍校的錄取通知書。軍人這一神圣的職業在他們家代代相傳。
解放戰爭 浴血戰場
“我父親楊再雨,16歲參軍,參加了遼沈戰役、平津戰役等戰役,26年的軍旅生涯讓他養成了堅毅的性格,而這種性格影響了我們后代。”楊繼明說:父親是河北唐山人,家人都是漁民,他8歲的時候父母雙亡成了孤兒,靠討飯為生,直至1945年9月,正在街上討飯的父親遇見了剛剛回鄉的大伯,當時大伯已經是特務連連長,就將父親帶到了部隊。由于父親當時只有16歲,就擔任了衛生員一職,并以這一身份參加了遼沈戰役、平津戰役,一直輾轉數千公里,跟隨部隊解放了數百座城市,最后抵達海南島。”
“父親雖然沒有在前線陣地扛槍打仗,但是也在戰壕里扛著藥箱穿梭在各個連隊間,為受傷的戰友包扎傷口、處理病情。父親說,戰爭是殘酷的,大家都很痛恨戰爭,但是為了新中國的解放事業,大家既都不顧生死、奮勇沖鋒,一個連隊一百多人,往往是一場戰斗下來,就會大量減員,最令父親難過的是,剛剛還有說有笑的戰友轉眼就陰陽相隔。”楊繼明說,在戰場上,父親和其他戰士一樣時刻面臨著死亡,一次在前線衛生院,敵軍的飛機不停地轟炸,父親協助大夫正在為傷員進行手術,突然一顆炸彈就從房頂上穿透下來,萬幸的是這顆炸彈并未爆炸,這次突如其來的危險,多年后父親仍心有余悸。
1950年,楊再雨所在的部隊轉為空軍,部隊命令他前往張家口航校學習空軍地勤相關知識。在那里,楊再雨完成了三年的學業,后被分配到位于太原的第十航校工作。1971年楊再雨轉業回到臨汾,從事臨汾紡織廠的籌建工作。
保家衛國 駐守邊疆
“我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在部隊大院長大,從小對部隊、對軍裝有特殊的感情,當兵也成了我的夢想。”1978年,楊繼明20歲,在父母親的鼓勵下,他報名參了軍,從臨汾出發,乘坐了七天七夜的悶罐車,到達了新疆吐魯番地區鄯善縣,開始了部隊生活。
吐魯番地區是小說《西游記》火焰山的原型,一年四季干旱少雨,白天烤死人,晚上凍死人,晝夜溫差極大。新兵連的日子,即新鮮又艱苦,由于楊繼明是城市兵,沒有農村兵體質好,所以吃苦更多。新兵連的艱苦磨練,讓他完成了由一個老百姓到軍人的轉變。
楊繼明所在部隊是雷達部隊,下到連隊后他成了一名報務員。部隊的條件十分艱苦,在地窩子(往地下挖一米,四周圍起來就是住所)里一住就是5年,直至1983年光榮退伍,復員后在臨紡參加了工作,繼續發揚軍人本色。目前,楊繼明擔任了臨紡托管處勞資科副科長,不僅負責退休人員的工資、醫療、養老等事務,還負責臨紡生活區的物業管理。
和平年代 傳承軍魂
2005年7月,對楊繼明一家來說是別樣的,因為楊繼明的兒子楊寬以593分的高分考上了國防科技大學指揮類專業。那年高考,一本錄取線為531分。通過查詢得知,楊寬已被北京交通大學錄取,但是倔強的楊寬還是毅然選擇要上軍校,也許是有著軍人家庭的遺傳與氣質,過五關斬六將,經過嚴格體檢、政審等一系列的手續過后,楊寬如愿以償被國防科技大學錄取了。
“看到楊寬的軍校通知書,老父親高興地拿出珍藏許久的軍功章,爺孫倆交流了很久。”楊繼明說:兒子考上軍校,意味著我們楊家第三代唯一的‘男丁’也成了軍人。兩年前父親去世了,他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楊寬能在部隊好好鍛煉,以優異的成績報效祖國。2010年楊寬畢業后被分配至38集團軍某防空旅,目前擔任連隊指導員職務。”
一家三代軍人,為祖國的安定繁榮奉獻一生。用楊繼明的話說:“無論馳騁在硝煙彌漫的戰場,扎根在寂靜的邊關,還是駐守在繁華的都市,一家三代軍人都會永遠銘記黨的恩情,永遠跟著黨,永遠忠于黨,永遠做黨的忠誠衛士。”
記者 蘇亞兵
倪敬南:三代從戎 男兒要當兵

倪敬南的父親(右)在朝鮮戰場留影。
臨汾新聞網訊 “我是軍人的女兒,也是軍人的兒媳婦。我是軍人的妻子,也是軍人的嫂子,還是軍人的媽媽。”提及自己的“多重身份”,家住市區功臣小區的倪敬南老人自豪不已。在她看來,家風是傳統,不能遺忘;家風是文化,需要傳承。而她家的好家風已傳承三代,那就是“家有好男兒,定要去當兵”。
1946年,整個中國處于黎明前的黑暗。倪老的父親為了民族大義,舍下尚有身孕的妻子奔赴戰場,一走便是7年。“在此期間,父親只往家寄過一封信報平安。至于他身在哪個部隊,參加過哪些戰役,信中絲毫沒有透露。直到村公所給家里送來光榮匾,我們才知道父親已參加抗美援朝戰爭。”倪老回憶,六七歲時,我第一次見到父親。父親的臉上掛著笑容,其中飽含著勝仗歸來與久別重逢的喜悅。”
短暫的團聚過后,倪老的父親趕赴北京一所軍事院校進修,她與父親相處的時間依然少得可憐。但是,父親每每回家探親,都會跟她講起朝鮮戰場上那些難忘的往事。“當時,父親和他的戰友被敵人圍困在一處深山,附近沒有水源,也沒有食物。他們忍饑挨餓地度過幾天后,一位戰友發現遠處有一種果子可以解渴,便主動要求前往。沒想到,那位戰友的行蹤暴露了,倒在了血泊之中。為了不讓戰友白白犧牲,父親只身一人去探路,不僅發現一條隱蔽的山路,還找到了水源,他們小分隊總算脫離險境。”關于父親的生死經歷,她的記憶依然清晰。
父親的一言一行影響了倪老一生,她時刻記得父親對她的教誨,即堂堂正正做人,正正直直走路。在她心中,所有的軍人都如父親一樣思想簡單、為人誠實、不怕吃苦,身上有著無數的優點。因此,當她到了適婚年齡,她的擇偶標準只有“軍人”一項。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她經人介紹與第一任丈夫相識、相戀,并走入婚姻殿堂。
“兩家人第一次會面,父親和公公一見如故。令人驚喜的是他們二人曾參加過同一戰役。這難得的緣分注定了我的身份這輩子都離不開‘軍屬’二字。”倪老娓娓道來,婚后,我們聚少離多。我的第一任丈夫返回部隊,投身于建設祖國的熱潮中。由于人手不足,他常常要一個人開車去裝沙、卸沙,還主動加班加點。凡是上級交代的任務,他保證完成且只多不少。”
倪老的第一任丈夫退伍后,仍保持著軍人的習慣。他對子女要求嚴格,從小給他們灌輸“一人入伍,全家光榮”的觀念。他于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病逝,但他的精神永遠活在子女心間,為他們照亮了前行的方向。兩個兒子不約而同地選擇從軍路,去部隊實現自身價值。臨行前,倪老總會千叮嚀萬囑咐:在軍營好好鍛煉,爭取作出貢獻,不要拖軍人之家的后腿。”
數年后,子女先后走上工作崗位,倪老的幸福便成了他們最牽掛的事兒。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她與第二任丈夫喜結良緣。“說來也巧,他也是軍人,還是位老八路。因為有著共同的追求和信仰,我們才走到一起。他參加過諸多戰役,也立下戰功。他時常給我講自己的抗戰經歷,曾經多少次徘徊于生死邊緣,曾經多少次品嘗戰爭勝利的喜悅。”倪老笑著說,我有著割不斷、舍不掉的軍人情結,這已經扎根于我的生命和血液。”
“我家男兒愛當兵,我驕傲、自豪、榮耀。”倪老希望這個好家風能一直保持下去,一代又一代續寫著軍人世家的傳奇。
記者 李靜
郝維烈:難解軍旅情 報國烙心中

臨汾新聞網訊 一人當兵,全家光榮。如果一個家庭在不同的年代,先后有五人當兵,這個家庭該有多光榮啊。
1938年,郝維烈和他的伯父郝鵬舉一起當了兵,當時,他15歲,他伯父五十多歲了,一老一少,很顯然都不是入伍當兵的最佳年齡,這伯侄二人是如何走進部隊的呢?
現居住在臨汾市功臣小區的郝維烈原籍山西省沁源縣榆坪村,1923年12月出生,今年93歲。郝老雖然年紀大,但精神矍鑠,思路清晰,回想起自己年少當兵的歲月,他笑得是那么的純樸甚至洋溢著童趣。
“我的家鄉當時很窮,由于戰爭,到處兵荒馬亂,為了躲避戰亂和土匪、散兵游勇的侵襲,老百姓只能躲在山上的窩棚里,生活得很艱難,家不像家。我小時候上過三年學,識得不少字,還參加了兒童團,一位親戚送給我兩本書,一本《論持久戰》、一本《共產主義宣言》,我連蒙帶看地看完后,很受啟發,當時就很想去當兵打仗,把日本鬼子趕跑,讓大家都能過上正常的日子。”由于兩本書的啟蒙,一個年少的農家子弟蒙生了革命的志向。然而,他的想法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對,因為郝維烈的父親兄弟三人,伯父未曾結婚,一個已故去,而他的父親又只有他一個兒子,所以他是三門獨子,全家人拿他當命根子,都不愿意讓他去冒險。得知郝維烈有當兵的想法,父親便帶他去找工作,想把他拴住。可是,一直都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郝維烈還是要去當兵。看他意志堅決,家里便把他“軟禁”了起來,讓人看著他,不讓他離開家。直到1938年冬天,因為剛下了一場大雪,大人放松了警惕,認為他不可能走了,然而,郝維烈正是抓住這樣的機會,跑了出來。
出了村沒多遠,他碰到鄰居高自勝到山上砍柴,由于二人平時關系不錯,郝維烈便對他說了自己的想法,高自勝很支持他的想法,告訴他離家五里路的一個村里現在駐著八路軍的隊伍,并送他過去。高自勝因為當時已經結婚并有了孩子,他便回了家,郝維烈留了下來。
當時,郝維烈留在了一個連隊,連長姓宋,指導員梁建功恰巧是他的一個表侄(郝維烈姑姑的孫子),雖然輩份小,年齡卻比他大,并且當時他還兼職當地的區委書記。梁建功深知他家的情況,看到表叔要參軍,立即讓他回去,但郝維烈就是不回去,被逼急了,給表侄撂下一句話:“不要我可以,反正我不回家,要不我就去別的部隊!”出了營門沒多遠,表侄又派人把他追了回來:還不如留在我這里,我還能照應你。”
梁建功帶著郝維烈回了一趟家,去給老舅(郝維烈的父親)說明情況,家里一看實在留不住郝維烈,便同意他跟著梁建功打鬼子。郝維烈的伯父郝鵬舉看到這個情況,出于親情,為了能更好地陪伴、照顧侄子,他也要求參軍:我做過廚師,部隊也需要做飯的,做好飯也能為打鬼子出力。”就這樣,郝鵬舉、郝維烈伯侄二人同時當了兵,在當地一時傳為佳話。
由于年齡小、個子小,郝維烈背不動槍,部隊就安排他當了勤務員,之后又當了衛生員,隨著部隊輾轉多地,他先后參加過關家垴戰斗、黃崖洞保衛戰、百團大戰、平漢戰役等。抗美援朝時,他隨部隊參加了第一、二、三、四次戰役,從一個衛生員成長為一個醫生、衛生連長、臨汾軍分區后勤部長等,副師級干部。
郝老的從軍生涯對他的孩子們產生了直接的影響,他有五個孩子,兩兒三女,其中三個孩子選擇了從軍之路。上世紀六十年代,他的大兒子郝理平正在石家莊某中學上學,到了可以入伍的年齡,于是報名參軍,從軍5年,樂于做普通士兵,在一次執行任務時,所乘車輛出了車禍,被撞成腦震蕩,復員后被安排在太原一家單位工作。
兒子有從軍夢,女兒也有報國志,郝維烈的女兒郝永紅(小名和平)在運城衛校畢業后被招入伍,成了原28軍84師師醫院的衛生員,3年后復員到臨鋼醫院,后又在臨汾衛校學習,前幾年臨鋼醫院裁人時,已經任職兒科主任的她積極發揮黨員的帶頭作用,響應號召,率先報名內退。
郝維烈最小的女兒郝津平曾經在堯都區神劉村插隊,后被招工到鐵路工作,沒多久,被招兵到28軍做了一名通信兵,服役期滿后復員,被分配到鐵路檢察院工作,成為一名普通的財務人員。
郝維烈1938年3月入黨、10月入伍,少年從軍,槍林彈雨,戎馬一生,曾被評為一等功臣,官至副師級,然而,他從沒利用自己的官職為子女們謀私利,他的五個兒女也沒有因為父親是高干而養尊處優。“家屬當年隨軍來部隊時沒有錢,路費都是娘家人湊的;聽人說女兒當年在部隊騎著三輪車買菜,別人根本看不出她是干部子弟,這都是我想要的結果。”
普通一兵,來自人民,為了人民,郝維烈一家三代5人從軍,深懷軍人情懷、部隊情結,那一抹軍綠是蕩漾在他家人心頭永遠的、最美的顏色!而部隊的培養,也讓他們不論在什么崗位從不搞特權、不擺架子,踏實工作,始終保持著普通軍人本色,這點,已經成為他們家庭的家風。
記者 韓曉芳
李順興:三代從軍路 滿腔報國情

臨汾新聞網訊 “我們的隊伍向太陽,腳踏著祖國的大地,背負著人民的希望,我們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李順興老人至今都能完整地唱出這首嘹亮的軍歌。如今,李老的大兒子以及老二家的孫子三代人從軍,軍人的品質和作風也融入到了他們家的日常生活。7月25日,記者在功臣小區的閱覽室內,見到了已過耄耋之年的李順興老人。在與記者的交談中,李老顯得有些興奮,幾十年前的往事,在他的言談中仿佛就在昨天發生一般。
先戰斗 而后參軍
李順興老人是一位參加過抗日戰爭的老革命,他的父親是一名地下黨員,經常教育他要成為一名戰士。今年,已經88歲的李老身體硬朗,聽力欠佳。當記者和老人交談時,他雖然聽著很吃力,但對自己的革命經歷記憶猶新。
李順興老人13歲就參加了革命,第一次參加戰斗是伏擊鬼子的運輸隊,帶著破草帽,守著地雷線,靜靜地等待著敵人的到來……首次參加戰斗就消滅了12個敵人,還繳獲了很多戰利品。也就是這次戰斗,讓他順利地參加了革命隊伍。
在以后的戰斗中,李順興還獲得過很多軍功章,其中的一枚軍功章對李老有著特別的意義。1949年在解放太原的時候,李順興在20兵團203師608團三營擔任通訊班班長,在戰斗中三連與大部隊失去了聯系,沒有電臺的情況下,部隊只能通過徒步通訊來聯系。李順興主動請纓聯系三連,與三連一起歸隊時,他們遇到了國民黨的一個連。敵人遠遠地喊話問:你們是哪個部分的?”李順興急中生智回答:我們是三連的,自己人!”敵人放松了警惕,被我軍全部俘虜。經過反復的作思想工作,他們全部自愿參加了人民解放軍。事后,部隊首長親自給李順興頒發了一枚軍功章。
傳家風 三代從戎
上世紀七十年代是激情燃燒的年代,能應征入伍穿上橄欖綠的軍裝,幾乎是每個年輕人的夢想。李順興老人的大兒子李建平,在父親的熏陶下,1976年他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應征入伍,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邯鄲某部汽車連服役。
在和平年代,雖然沒有了戰火和硝煙,但是,李建平卻把部隊安排的每一次任務都當成一場“戰斗”。服役期間,他曾駕車多次圓滿完成危險而又艱巨的任務……夏天暑氣蒸騰,李建平和戰友們堅守在有限的卡車駕駛室內,衣衫經常被汗水濕透,還要忍受蚊子的“侵襲”;冬天滴水成冰,李建平駕駛帶著防滑鏈的物資運輸車,行駛在蜿蜒崎嶇且堆滿積雪和暗冰的山路上……
在軍人世家環境、氣氛的熏染下,李老的孫子小李從小就對軍營充滿了向往。“長大后要成為軍人……”這樣的夢想已經深深扎根在他的心里。2012年畢業后,他也光榮地參軍入伍,在部隊上還獲得過先進個人的獎項。
“兒子從小就以爺爺為榜樣,他爺爺那些打仗的事情,他都耳熟能詳……”李老的二兒子李戰平說,孩子在部隊的時候,每次都是報喜不報憂,摔傷、碰傷是經常的事兒,可他從沒和父母說過,因為老爺子常說,當兵訓練哪有不掉肉的,受個傷算不了啥,立了功才是自己和家人的光榮。所以孩子受到部隊的獎勵時,在第一時間給家人打了電話。
李順興老人一家三代參軍從戎,那一身身的軍裝,是老人和兒孫對部隊的情懷。李順興一家三代從軍,不一樣的年代、不一樣的歷史背景,但是有著一樣的信念、一樣的追求、一樣的情懷,譜寫的是一曲中國普通家庭報效祖國的豪邁贊歌。
記者 郝海軍

責任編輯: 吉政